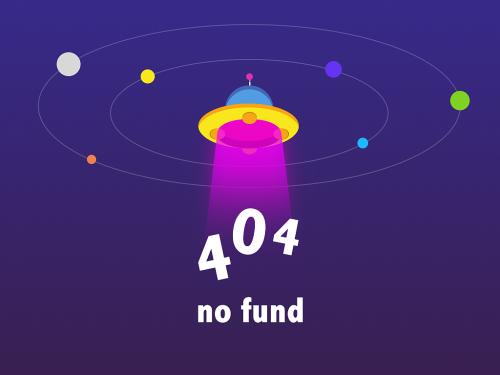【北大国发院博士论坛】第5期,韩毓海:从永贞革新到改革开放
【北大国发院博士论坛】第5期,韩毓海:从永贞革新到改革开放
![640[1]](/uploads/image/images/2ae82cdc27da46c9b3f01118361c0fa9.jpg)
5月22日晚【北大国发院博士论坛】第5期,韩毓海教授是抱着一大摞书上讲坛的。看得出来,那些书都已翻旧了。是些什么书?在演讲中可以找到答案。
以下为韩毓海演讲全文:
主 题:公元十世纪以来中国的改革与革命:从“永贞革新”到改革开放
主持人:席天扬(北大国发院副教授)
主持人:今天的活动是由中信改革发展基金研究会、中信出版集团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大国发院国事论坛联合举办的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的第三期,也是【北大国发院博士论坛】第5期。
今天是一个春意盎然、阳光明媚的好天,从大家的表情上感受到大家对这次讲座的热情。在今天的中国没有第二个话题像改革这样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引发热烈的讨论和思考。大家都知道,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决定》,2014年被称为改革元年。
如今一年的时间过去,关于改革的成效、进展,从学术界、理论界,到政界、民间有许多热烈的讨论,我们为改革进步取得的进展而感到骄傲的同时,也为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暴露出的新问题而感到担忧。对中国来讲,中国最大的优势不仅在于我们是一个大国,而且我们有两千年的文明和历史,当我们在思考人类的改革、经济制度的时候,不仅要向外看,还要向我们的历史去看。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比今天接下来给我们做讲座的韩毓海老师更适合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
韩毓海教授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也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咨询委员。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严肃的学者,更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他的作品《500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获得2010年度全国优秀图书排行榜总榜第一名,今天下午我一直在读韩老师的《500年来谁著史》,觉得有一种惊风雨、泣鬼神的感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宽广的视野;二是韩老师的思考和研究已经超越了文学、历史的范畴,而是综合了人文社科的各个领域来思考关于人类制度,我们的经济、历史、社会、政治的终极问题。这就是我们的道路是什么、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会站在今天这个地方,我们要何处去。
非常高兴能够请到韩老师为我们分享。要特别介绍的是,我们知道韩老师的新著马上就要出版,是关于中国过去500年来的改革。今天的题目是“公元十世纪以来中国的改革与革命”。今天来到这里,我们是非常有幸的,韩老师不仅把他即将出版的著作的成果跟我们分享,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对过去500年来改革与革命的思考,而且可以聆听他关于公元十世纪以来的1000年来的改革和革命的思考。
下面欢迎韩毓海教授为我们做演讲。
韩毓海: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和褒奖。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大家晚上好!
很抱歉,我明天一早要出国去,许多工作还没有准备好,行李没有打,心里没有谱,这种心态下,不适合讲一千年来的大政方针,但因为这个事情是早就安排好了的,我只能硬着头皮大胆地讲一讲,今天,孔丹同志在百忙之中亲自来听我的汇报,我要表示感谢和歉意。
还要抱歉的是,我要改一下题目,就是把题目里的“改革与革命”,改为“治理”。也可以说,戏还没开始唱,我的戏码就变卦了。
我们知道,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主席主政以来,有一个词,大家在各方面都会用,就是治理。比较全面地阐释治理的问题是2014年的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收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当中,题目叫做“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刚才主持人说,今年是改革元年,其实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每次三中全会的主题都是改革,但是,这一次不同,因为这一次总书记讲改革时,用的词是治理,不仅是改革。
在这篇文章当中,总书记对治理做了非常重要和独特的阐释。自从有了治理这个说法以后,许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说,我们很长时间都在谈治理。还有人说这个治理是我早就提出来的,或者,治理这种说法是外国某某人提出的。当然,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人无疑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但是,学习了总书记的讲话之后,我觉得他有两点,是跟我们学校里的人谈的治理是完全不同的。
第一点,他是要从宽阔的历史视野去看治理。他说我们的治理经验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西方社会的治理经验;第二个部分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治理经验;第三个部分是社会主义的治理经验。我们应该从这三种治理经验和教训当中,从宽阔的历史视野来理解治理的问题。这是总书记在讲话当中很鲜明的一点。他其中特别谈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说“有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并不意味着就有很强大的治理能力”。反过来说,有强大的治理能力,也未必有完善的治理体系。我们中国几千年来并不是没有一个治理体系。当然,我们对这个治理体系缺乏系统的总结,以至于在日本发生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人倒是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汲取了中国的治理体系——包括朱子学、阳明学等。当然,更主要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日本出了20多种版本,当时中国清王朝对这个东西的理解总结不够。我们到日本去,跟日本人交流,他们很直率地告诉我们日本的明治维新并不是日本单纯的学习西方的结果,主要是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中国治理体系的治理经验的结果。
我们在1840年以前,并不是没有治理体系,而是缺乏对这个治理体系的总结。同时,在晚清的条件下,这个治理体系没有转化为治理能力。反过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90多年的奋斗当中表现出了强大的治理能力,驾驭战争的能力、驾驭经济的能力。但是,我们现在是否形成了有效的治理体系呢?从长治久安的角度来说,未必是这样。
总书记在北大跟我们大家座谈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他说“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什么会在鸦片战争以后陷入了积贫积弱?”原因是什么?他当时说“看来,我们的治理体系不仅仅是在清朝的中后期出现了问题,恐怕在明代,1500年左右就发生了大的问题。鸦片战争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接着他就问林毅夫教授,“毅夫老师,你觉得是这样吗?”林老师就说,“我当然觉得是这样”。总书记接着问:“你认为这里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总书记心里是有答案的。在后来给院士的讲话中,他从某种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
总书记在对两院院士的讲话中,他讲到清王朝并不是一概的拒绝科学技术。总书记自己去考察,他说“康熙皇帝曾经请了大量的传教士来学习西学,他自己关于西学的笔记就有几十本。在天文学和地理学方面,他的造诣都是很深的。而且,《皇清全域图》经过传教士的协助,是世界上最好的地图。但就像鸦片战争以后魏源的《海国图志》没有在中国起到作用,在日本起到作用一样,这个地图没有在中国产生作用,反而在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总书记说“并不是因为不学西学,而是我们把西学当成一个上层社会的秘密的知识,藏之于深宫,变成了秘籍,而没有向全社会普及”。他讲到“单纯的科学技术如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将会是怎样的”。中国并不是没有博学的知识分子,而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跟实践结合,是动手不动脑的阶层。他们不是知识不行,思想不行,是办事不成。造成中国在近代落伍,在诸多原因当中,这是很重要的因素。因此,中国的现代转变,必须是知识分子的转变、知识方式的转变和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变。这是总书记谈治理问题的时候,所表现出的深刻的历史视野和对历史转换的非常独特的认识。
同时,他在谈治理的时候,跟一般的学者不同的另外一点,就是他谈的治理固然是政治、经济、财政、司法,但绝不仅仅是这几方面。因为治理在他那里,还包括了“治心”的问题。他在今年两会期间,在贵州代表团讨论的时候,讲到王阳明。这不是他第一次讲王阳明。他在贵州视察的时候,就跟贵州大学的师生讲王阳明,讲到“治世容易治心难”,这是一般谈治理的学者不会想到的。什么是心?什么是仁心?我觉得这涉及到政治伦理的问题,这是治理所包含的很重要的内容。
用王阳明的话来说,仁心是仁术的起点,没有仁心,仅仅流于术,你这个治理就完了。什么是仁心呢?就是从一个国家、从一个民族最长远、最根本的利益去考虑问题,政治是这样,治理也是这样。它不是一般的政治、经济、财政、司法这些术的东西。这些术的东西当然重要,但绝不是全部。
我要说的就是,改革与革命,不如治理这个说法好,而我们对于治理这个词的理解,是需要对照总书记的那些讲话,有所深化的。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也是孔丹同志的意见。今天孔总坐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他是怎样启发了我。
上周孔丹同志找我去,跟我讨论,孔总在那次的讨论中提了很重要的问题,他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就是改革。据考证最早提出改革的是管仲。于是管仲变成了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我当时就插了一句话,我说,发明改革这个词的人确实是管仲,但是,南宋伟大的政治家叶适也曾经说,中国的政治坏就坏在管仲身上。我后面会讲,叶适为什么会这样批评管仲。
孔总接着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我们用改革和反改革这种词语来描述中国历史,可以吗?历史是这样简单的吗?我们能用这样一个简单的线索来观察历史吗,究竟是用改革来观察历史呢?还是像总书记所说的那样,衡量我们的政治行动,应该是以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旨归呢?我想这就牵涉到我们刚刚说的治理与治术的问题。
在《资治通鉴》的开篇,司马光引了一段话,很有名,有人问孟子说“张仪、苏秦这些人,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他们纵横捭阖,像管仲一样,很迅速地使一个国家兴起,变成富强的国家。他们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大丈夫吗?难道不是伟大的改革家吗?而孟子的回答是:“诈人也,圣人恶诸”,圣人其实不与这些人为伍。什么是圣人?什么是君子呢?他说“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后面的话很著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为大丈夫”。他在这里谈了什么是政治的根本。
在清朝初年,有一个湖南人,反复抗清失败,躲在湖南的深山里写书,这个人是王夫之,也就是王船山,他写了著名的著作《读通鉴论》,也是跟《资治通鉴》有关。他也讲了这些问题,历史上那些能吏、大吏,在历史上的作用就是正面的吗?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王安石。他说王安石这个人是一个妄人,此人最大的缺点是不实事求是。大家知道,王安石说动宋神宗改革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宋神宗问他“您看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效法和模仿唐太宗呢?”王安石回答说“皇上,您怎么能这么想呢?您比唐太宗强太多了,您应该效仿尧舜禹”,这个话就是典型的忽悠领导。他为了推行他的主张,为了推行他的学说,不惜说假话。当时虽然宋朝立国已经一百多年了,可是神宗还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神宗极想有为,而对这样一个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年轻人,是不能采用忽悠的办法的。因此,王夫之说王安石简直跟我们本家韩愈有一拼。因为他告诉皇帝说您按照我的做就行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继承了先王之道,您就按照这个先王之道来做。韩愈也说“文起八代之衰”,孔子的学说传到孟子,孟子的学说不传了,传到他韩愈,后来王安石、康有为这些人都自称圣人,认为自己继承了先王之道,这种先王之道,就是康有为所谓的改变与变法。中国历史,大致从戊戌变法之后,就变成了改革与变法的历史。
孔总有一句话说“纵观我们党在历史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的决策,都不是依据十全十美的先王之道。都可以说是艰难而痛苦的选择”。与其研究那个,不如研究中国共产党艰难的决策过程。我们的每一次决议、每一次抉择都不能说是十全十美的。因此,一个真正的负责任的领导,或者王夫之说“大臣之道”,是什么呢?在给皇帝进言的时候,起码要把两面都说到,不要把事情说得天花乱坠,打保票。因为最后的结果往往出乎意料之外。
不能忽悠领导的同时,更不能忽悠群众。因此王船山还说,一个真正的好的政治家,不能从于流俗之毁誉,他批评了汉宣帝时的赵广汉,也批评了宋代著名的青天大老爷包拯。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批评他们邀名,搞民粹主义。像包拯和赵广汉这样的人太短视,往往为了满足老百姓一时的冲动,而与群众互相忽悠,而没有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的安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此所谓“流俗趋小喜而昧大体”。“不欲求快于一时之心也。心苟快,而天地和平之气不足以存,俗吏恶知此哉?”一个好的领导人、一个好的大臣,应该像谢安拒桓温、抗苻坚那样,做了救民于水火的大事,而“民不知感”。能够像郭子仪困厄期间一样,在遭受诽谤的时候,“而众不为伸”,这才能算是有独立的政治人格。你不能说因为你自己的冤屈和清名,就搞得天摇地动,你一出事,老百姓就上街为你申冤,结果江山社稷都差一点被颠覆了。你要以社稷为重,要心态平和,不要总是很亢奋地鼓与呼啊。忽悠领导固然要不得,忽悠群众同样要不得啊。因此他说,一个政治家之用与不用,都不能根据一时舆论之欢呼和怨气之伸张为标准,这是很有意思的想法。
王船山说圣人无名,大臣无党,政治家无家、无偏私,他提出了很重要的政治伦理问题,这就是公。一个政治家为什么要有仁心?除了有治理的经验和才能以外,因为他是公家人,而公家人必须无偏私,极而言之,帝王无家,以天下为家,你走了政治这条路,就等于出家了,政治家无好恶,以国家之好恶为好恶,这就是仁心,仁心是仁术的基础。
这就是总书记经常说的,功成不必在我,我们在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当中,前赴后继地前进,一切的行动和作为都不是为了个人逞能,都不是为了邀名,不是为了扮演改革家,而是为了从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的长远利益来打算此时此刻的行动。我们每一个选择都是艰难的痛苦的选择。只有从这两个一百年和宽阔的历史视野的角度考虑问题,才能做到我心光明,才能放下这些改革与反改革、成功与失败,才能够勇敢地前进。
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为什么从十世纪的“永贞革新”说起。我下面介绍的题目,每一个都要介绍一个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同时介绍他的一篇文章。
“永贞革新”,给大家介绍很熟悉的柳宗元和他的《封建论》。毛泽东主席非常喜欢柳宗元的《封建论》,他给郭老写过一首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不但如此,毛主席对于柳宗元的命运,以及所谓“永贞革新”中二王八司马的命运都非常的怜惜和感慨。
![640[1] (2)](/uploads/image/images/b5dd7448cc9f4566919bd6432f3b1051.jpg)
为什么柳宗元的《封建论》那么重要呢,因为讨论中国的政治与治理,第一个问题就是统一和分裂。在中国做治理者,摆在面前的第一位的问题,或者根本的底线,就是国家的统一与分裂。无论什么样的原因、理由陷国家于分裂,那就是最大的失败和失职。柳宗元的《封建论》讨论了这个问题。
大家说,建立一个大一统的、统一的国家,这并不是唐代才出现的问题,中国的统一是从秦就发生了的。但是,历朝历代的治理者都在思考一个问题,秦如此富强,为什么如此短暂?隋如此富强,为什么那么短暂?汉和唐则不然,这里的原因是什么?中国为什么自秦以来还是反复的经过了战乱和分裂呢?
两千年来有两次最后的分裂,一次分裂就是发生在“永贞革新”之前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大概是前一千年的最后一次巨大分裂。还有一次就是清王朝崩溃以后中国所陷入的那个军阀混战的局面。
“永贞革新”就发生在这个时期,秦朝虽然用强力把一个国家捏起来,但它靠的还是武力,秦朝以及后来的几个王朝,还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使这个国家凝聚起来的办法。那个办法是到安史之乱以后方才走向成熟的。这个办法的核心是统一的中央财政和税收。这个问题是在安史之乱当中表现出来的。唐朝最大的问题,就是随着疆域的扩大,开始出现了各个地方的藩镇和刺史。而藩镇和刺史最大的特点是有税收权。
安史之乱结束以后,唐德宗时代的宰相杨炎提出两税法的改革,这是公元780年。这个时候第一次有了中央的财政预算,就是要计算皇帝和国家会花多少钱。以前是需要钱就花,财政是个无底洞和一锅糊涂账。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明白,一共需要花多少钱,这就有了个定额,有了预算。有了预算以后,就可以把预算摊派到各个州郡去,州郡长官的主要任务就是管理财务和税收,地方官员的主要职责就是这个财政包干。而对老百姓来说,就是夏秋两季收税,谓之两税,当然,两税法是不是真正的落实了有很多争论,但是两税法公开免除了徭役。这就是完成了从徭役制的国家向赋税制国家的转变。我们知道秦朝崩溃的原因就是徭役。陈胜、吴广是服徭役路上反了的。同时,这个转变就使中央领导下的文官政治有了抓手,文官做什么呢?文官的主要工作,也就是后来宋朝所说的三司的工作,就是国家的税收、预算和财政,就是把地方上的钱财物转移集中到中央。
“永贞革新”发生在唐顺宗的永贞元年,也就是公元的805年。唐顺宗是一个残疾皇帝,顺宗失音,不能决事。他的国家大事由王叔文和王伾两个人决定,就是二王八司马的二王。他们两个人是翰林学士,唐顺宗时代,翰林学士是负责起草诏令的。唐朝是三权分立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为什么会有分权、有三权分立呢?世界上有贵族的地方,就有分权,三省制度是建立在贵族制度的基础上的,有负责给皇帝起草诏令的,有把诏令传给贵族院的,有同时负责贵族院的驳回的。翰林起到的作用和尚书令是一样的,就是可以起草诏令。
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把中国的贵族制度消灭了,“二王”他们两个的出身不是贵族,而是经济和财政官,都是做户部和度支起来的。因此,围绕着他们形成了一批从财政和税收的角度,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由专业化的官员构成的小团体,他们主要要做的就是把各个藩镇的财权和税收收归中央,这是真正的中央集权的开始。这个是“永贞革新”的实质。
上世纪90年代,我们国家也出现了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严重的不平衡。在那个时候,江泽民同志和朱镕基同志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搞中央地方分税制,我觉得有点像“永贞革新”时做的事情。
在这个治理集团当中,有两个我们中文系的人混在里面,一个叫柳宗元,一个是刘禹锡。柳宗元不知为什么因为中文系而出名,他祖上几代都是做大官的,他其实是政治家,是山西河东人,祖上在北魏时代就是朝廷里的大官,河东柳氏,北魏、隋、唐以来是历代卿相,他生在首都长安,是一个真正的干部子女。很年轻的时候在朝廷里做监察御史,吏部侍郎,类似于中纪委的工作。刘禹锡做的是盐铁转运的工作,纯粹是国有经济的工作。当时盐铁是国有企业,像今天的两桶油。这些人当时认为,唐顺宗虽然身体不好,失音,不能理政,可是他并不糊涂,应该支持他做这个重要的治理转变工作。
当然,还有一批人,贵族的余孽,特别是各个藩镇的地方势力和宦官,他们认为这个转变不行。于是,他们很迅速地推了顺宗的儿子宪宗上台。但宪宗上台以后,几乎却是完全采用了“永贞革新”这些人提的政治举措,使一个徭役制的国家向赋税制和预算制的国家转变,加强中央财政。国家统一的基础是财政和税收的统一。这些战略他都采用了,干得比他老子还好。但是,宪宗皇帝非常恨这些忽悠改革的家伙们,心里说你们竟然让我残疾的老子继续干,不让我上台。于是就把他们这些人远远地贬到很荒凉的地方,去当司马这种小官。刘禹锡最早被贬的地方是播州,就是遵义,后来改贬郎州。柳宗元先被贬斥到了永州,因此就成了我们文学界的人,因为他写了《永州八记》。
柳宗元这个人和另外一个干部子女的性情大不一样,那个干部子女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王阳明。王阳明的父亲王华,是南京的兵部尚书。王阳明也被贬,贬到很远,也是贬到贵州去了。王阳明被贬官,反而龙场悟道,以为得了自由了,觉得离开皇帝身边很好,没人管了,不是很自由吗?而柳宗元被贬到永州以后,却非常痛苦,时时刻刻想回中央,因为他就想不通,他认为自己的政策建言是完全正确的,皇上也很清楚这一点,他在用我的政策,干嘛惩罚我?于是,柳宗元就不断地给他在朝廷里的关系写信说,给皇上捎个话啊,请他给个机会吧。就像小平同志当年不断给主席写信一样,我还很年轻,我挺有本事的,让我回中央工作吧。
十年以后,终于来了机会,皇帝准备原谅他了。这些小司马们,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当时的首都长安。
这个时候,刘禹锡偏偏又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我们中文系的人是不牢靠的,他在元和十年写下《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皇上看了,怎么,你不服气啊?再怒之下,这次把他们贬到更远的地方。柳宗元从湖南永州,贬到了广西柳州,最终就死在了那里。他死的时候与曹雪芹一样,都是48岁。所以,我常常想,我这个人活到了49岁,这很不容易啊,比柳宗元、曹雪芹可是强多了。
在这个过程中,柳宗元写下了著名的《封建论》,他说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是统一,而不是分裂。他说秦朝之所以崩溃的原因是“在治不在政”。政治体制是好的,是统一的制度,治理方式是错的。原因是因为秦始皇太勤政,对下属的要求太严格。层层加码,最下层受不了,就反了。
他总结汉朝为什么出现衰落?汉朝乱的都是封国,州郡没有一个能造反和敢造反的。因为州郡的委任状和财政供给是国家提供,只有封国的人才有财政和军事的裁度权,所以,只有封国才敢造反。
唐朝的问题,不在州郡,而在藩镇,不在州官,而在藩镇有兵。在于国家不能节制藩镇手里的乱兵,也不能节制乱民。唐朝州郡的官员有一个造反的吗?一个也没有,因为他手里没钱也没人,缺乏造反的资本。因此,柳宗元说寻找统一的办法,就是要把兵权、财权收归中央,这个是中国政治的第一命题。他说封建是大私啊,是贵族们为了私其子孙,就要把兵权财权土地传给子孙后代,封建制就是土地私有制,因为土地是最大的资本。反过来说,统一是大公,秦始皇才是真正的大公至正之人,“始皇负衿而有天下,而子孙为庶人”,秦始皇没有分封自己的子孙,所以,地方分裂就没有基础,秦亡后乱了一下,但并没有回到战国时期的分裂,而又迅速统一,原因在这里。
我们谈治理,为什么要从“永贞革新”这儿开始?日本的学者说,中国的政治从唐代和宋代发生了变化,谓之“唐宋之变”。京都史学派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国为什么自宋以来基本结束了地方的封建割据,从此是统一的?这是因为统一是需要物质条件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特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中讲到,中国跟欧洲相比是气候不同的国家,相对欧洲来说,中国比较干燥。因此,中国土地的耕种比较依赖大规模的公共水利设施的建设。如果离开了公共水利设施的建设,个人的耕种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在中国先天的不具备土地私有化的条件。大规模进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这就成了中国历代王朝最基础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终于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工程,就是大运河。正是这样一个公共的工程,把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沟通起来。中国长期大一统的原因,就是这样的物质条件。我们所谓的“公”,是指公共工程、公共财政,这是历史转变的物质条件,我们所谓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就是这样的。
日本的京都史学派也认为,唐宋之间发生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交通。中国的首都,逐渐从西安移向了运河沿岸的城市:开封、杭州、北京。由面向欧亚大陆核心的长安,经过运河的勾连,开始面向东南沿海,这是唐宋之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日本学者没有看到,恰恰是柳宗元揭示出来的。这就是除了物质条件外,还需要制度条件和制度保障。为什么从那以后,中国的政治稳定有了保障呢?宋代以后,中国的几个王朝长期维持了统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官政治真正的确立。从贵族政治,到文官政治,这是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文官知道做什么。他们很重要的工作不是过去的三省,即中书、门下、尚书的文化、礼仪治国的制度。我们说中书、门下、尚书,这与其说就是民主制度,还不如说它实质上是贵族制度。而经历了永贞革新之后,这个贵族与皇帝分权的三省制度,就变成了技术文官执政的所谓三司制度。国家治理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国家的财政、预算和经济、司法这些内容,而不是过去贵族擅长的礼仪、词赋和经史。这是很重要的转变。正是因为这些工作的转移,使中央的财政制度能够确立。
第二个问题,我跟大家讨论一下1608年,北宋的熙宁变法,也就是王安石的变法。也介绍一篇王安石的文章,《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640[3]](/uploads/image/images/324226d3a8e344fc9e1cb6ae810a6aad.jpg)
首先从一个中文系的例子说起。大家都知道苏轼的著名的中秋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苕溪渔隐丛话》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对于这首水调歌头,大家的解释是怀念他的弟弟苏辙。但这是很肤浅的。对这首诗最准确的背景解释是这样的,王安石的改革引发了朝内新旧党人的激烈党争,所谓正人君子都反对他,苏轼也是其中之一,熙宁二年,王安石请建学校,罢词赋、明经诸科,苏轼立即做《议学校贡举状》,强烈反对。当时王安石是宰相,已经五十多岁了,苏轼才三十多岁,算是初出茅庐,结果,他就被从京城赶出来,先是通判杭州,熙宁七年,苏轼以弟弟苏辙在济州(济南),求知密州,也就是今天的诸城。水调歌头写于熙宁九年,即1076年,《资治通鉴》卷71说,这一年八月,新党下令,要把天下的庙宇、祠堂私有化,卖给私人,收取净利。这件事被旧党抓住,上告到皇帝那里,神宗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帝震怒”,这也成为新党和王安石失势的一个标志,这一年的十月,王安石被罢相,熙宁变法从此失败。
皇帝震怒这个事恰好是在中秋前发生的,立刻在朝野传开了,旧党都说王安石这小子要倒霉了,他要下台了。于是这些反对改革的正人君子,司马光之流都非常高兴,其中就包括苏轼。苏轼听到这个消息就喝得大醉,想他和他弟弟苏辙会不会因此又回到朝廷呢?于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政治方向是怎样变化的呢?那个时候他们是官员,不是我们这种纯文学工作者。他写的诗完全是政治化的。而且他们是很有政治经验的,苏轼明白:即使王安石倒台,但朝中新旧两党之间的互相倾轧已经盘根错节,即使回到权力中心,也是风险重重啊。于是,“我欲乘风归去,但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事实上,果然不出苏轼之所料,王安石倒台,他也没得好,在元丰二年发生的“乌台诗案”中,苏轼几乎丢了性命。
列宁把王安石称作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在发动改革之前,他担任的职务,恰好是三司度支判官,就是财政官。他要改革的心是早就有了的。他在上任三司度支判官的时候就写下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治理文献《上仁宗皇帝的言事书》,是万言书,写在宋神宗的爷爷宋仁宗的时候。他在当中提出的思想,也就是后来经常被大家传诵的名句,就是在《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里面说的那些话,宋朝要把历代财政官员副长官的名字题在墙壁上,他为这个墙壁写了一段话,“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杰大而后能如是,天子犹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很显然,他把财政、税收、国家的预算看得很重,没有钱是办不了事的。大家都讲三代之治,但三代之治的时候,大家都很穷,而现在不同了,没钱办不了事,抓不住财权,是要丢江山的。
因此,在《上仁宗皇帝的言事书》中,王安石开头就说到,宋代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皇帝是一个好皇帝,你简直可以比尧舜,简直比尧舜还辛苦。为什么国家治理一团糟呢?原因就是国家没人才。可是,每天这么多的人才在考试、选拔,怎么就没人才呢?他说,因为我们选拔人才的方式不对。人才的教、养、取、任皆不得法。结果,按照这种办法选出来的,不是废物笨蛋就是坏蛋。
怎么叫教不得法呢?他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国家的财政、税收、司法和军事。可是,我们现在教的都是课试文章,学的都是经史词赋,让一帮只会考试的人、中文系的人来治理国家,这非完蛋不可。他们会写材料和诗,会考试,会谈思想,但是,他们不懂政治、经济、财政、司法。所以说,教不得法。因此,必须废词赋明经,扫除课试文章,建学校,改革应试教育。
养呢?他认为也不得法。他说,财政归于中央,于是中央有钱了,就养了大批的官员,官员系统搞得很复杂,文武分开了,官与吏也分开了,历代从没有像宋代养这么多官。他说既然有这么多官员,再大的财政也担负不起那么大的办公费,于是,官员的薪赋很低,还不断的降薪,可官员也是人,他也要嫁女、娶妻、葬老人。那么点钱,根本就不能做个体面人,东西一多,自然就贱了,官帽子也是这样,官帽子太多,就不值钱了,实际上他就不是个体面人。在这样的状况下,你不逼着他贪污吗?所以就是养是个大问题。
取,他觉得也很有问题。他说历朝历代都是能够选拔有能力的人,简而言之,按照能力,择贤而用,但宋代却是一切都是按程序走,每一个职务都要干过,每个台阶都要待过。实际上这样选拔出来的干部,其实每一个工作都没干会,因为干一段时间就调走了。最后到了50岁,就把他调到首都去了。结果这个人什么都不会。或者说,他什么都会一点儿,其实什么都不会。既然选拔就是走程序,那么官员只要不干事,就不会犯错误,于是按部就班升上去的,大部分是笨蛋和庸人。所以取也不得法。
任,他觉得也不得法。对官员,没有一个考核办法。我们用什么考核他呢?科举考出来的人中文系的,治国理政怎么考察呢?如果用考试的办法,这些人就会考试,但办事一团糟。加上官不久任,屁股还没捂热,人就调走了,留下的都是半拉子工程。
因此,王安石认为宋代的根本问题是在顶层,干部队伍不够专业化。如果说改革要做顶层设计,顶层设计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要进行专业化。就是按照干实事的标准,去改革组织路线。干部干部,就是会干事的人,能为国家干实事的人,但组织路线出了问题,选拔出来的却是不想干事、不会干事、也干不出事来的混混,我就想起小平同志当年讲的一段话,他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干部,其实从人数来说也不是很多,我们的问题主要是不够专业化。不够专业化怎么办呢?当然就是学习喽。
第三个跟大家分享的政治文献是《外稿》作者是南宋时期的政治家,叫叶适,他是永嘉人,也就是今天的温州,这个地方出了很多的人。
![640[4]](/uploads/image/images/297571a6e82848fcb5c6da932a3409b5.jpg)
这个人在南宋非常危机的时候,不断地出来做事。他先是做平江,也就是苏州的官员。在苏州期间,他写了很著名的政治作品,就是《外稿》。我们大家研究中国治理的时候,往往不注意叶适这个人,因为他的词写得很臭,按照中文系的标准简直不入流,但是,他的《外稿》是第一流的政治文献,可惜读过的人不多。后来他做了工部侍郎兼国用参济官。南宋北伐的时候,他提出很重要的想法,就是到江北去开辟武装根据地,建立堡坞来安置流民。
他有非常多重要的见解,举一个例子。他在《财总论一》里说,三代都是重实的,这个实是什么?就是指仁心和民心。而与三代观点不同的就是管仲,因此管仲标志着中国政治上很大的变化,因为他开始重财,他认为的“实”就是理财。而汉宣帝就继承了管仲的想法。汉武帝和秦始皇就是王霸之道。所以,汉代的时候就把财而不是人心当作实际了,到了魏晋,江左是重名,但这个名却变成了重词赋,词赋完全虚的、贵族的东西,重词赋,这是重虚名的极端,那还不如重财赋呢。我朝大宋,更加等而下之,宋代也重名,宋代重名也就是重法。法是什么呢?就是程序。所以宋代简直是名实皆失,因为选拔的标准既不是三代的为人民服务,也不是秦汉的富国强兵,而是一切按照程序来,这样,国家和人才,就被僵化的程序给困死了。
我记得朱苏力老师讲了一段话,他说我们不能什么事都迷信法。他的观点跟叶适很像。他说我们改革开放那是法治的结果吗?那是小平同志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又画了一个圈,就改革开放了。如果按照祖宗的法,一切按程序来,哪会有改革开放呢?宋代的问题,所谓重名,也就是重法,一切都是按照程序来。宋的问题不是没有法,而是法太密,法太虚,法脱离了富强和民心,于是两头皆失。
叶适说,“隋最富而亡,唐最贫而兴”,关键在于帝王不重视民心,而重视财富,他认为这是舍本逐末。盐利起于春秋,田税起于鲁国,秦皇汉武欲求富强而有国家财政制度,但是,他的失在于人心。隋朝是很富的王朝,但这是一个无心的王朝。秦也是这样,它是无心的,统治者无心,结果无心失天下。他失去的是民心,并不是因为不富、不强。怎么叫失人心呢?就是执政者的功利心压倒了平常心,执政者一旦丧失了平常心,他就不能理解老百姓了。这就是他所谓“国无骏功,常道先衰,士无奇节,常心先坏”。
读到这里,我就很感慨,我年轻的时候,读西方社会科学的经典,感觉西方的社会科学,重视的是人心。霍布斯讲人与人之间是狼,斯密讲交换是人的天性,马克思讲人是劳动和交换的人,弗洛伊德讲苦难创造了文明,西方政治理论的一个特点是立足人心,有一种面对人心和震撼人心的力量,这是基督教的影响。如果政治和治理就是富国强兵之道,那么这样的政治就没有真正的力量,就没有面对人心的力量。
叶适批评王安石的治国就是理财的说法,指出这种说法特别是起于唐代中期的“永贞革新”,到了宋代最盛。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一大批病民的胥吏,后果就是为了财赋和经济的增长,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叶适这里提出一个问题,王安石当然也看到,但却没有引起他高度重视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官员队伍是由官和吏这两部分人构成的。王安石虽然说要提升官员能力,把那些非专业化的人转变成擅长财政、经济、司法的专家,但这种设想根本没有推动。原因是让顶层结构自己改造自己,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上层本来就不屑于财政、经济、司法这些碎事,他们知道的大事就是看文件。而知道财政、司法、税收的人是胥吏,即官员的幕僚和助手。中国的干部队伍是由官和吏构成的,官与吏相加,所以人数很多。官员是公务员,他可以逐渐地升迁,只要不犯错误按程序就能上去。胥吏呢?不是公务员,他就是事务员,就是管财政、经济、司法等等这些碎事的。实际上这个国家是由谁治理呢?当然不是没人治理,其实就是这些胥吏在治理。胥吏是没有工资或者工资很低的,他就是靠办事得好处费,党纪国法,能够治官,但却不能治吏,官员无为,胥吏胡为,国家不乱那才怪呢!
《水浒传》当中最典型的事务员就是宋江,宋江不是官,他就是办事员。他非常了不起,透露一个信息给晁盖,刘唐就跪在他面前,给他送一百两黄金。而且真正的问题是官员在不断地调走,而胥吏永远待在地方,永远不动,而且师徒相承、子孙相继。浙江就是出胥吏的地方,鲁迅的家乡绍兴就是出师爷的地方。
这个政治制度的分裂,在叶适的文章当中叫做“胥吏之害”,也叫做“官无封建,吏有封建”。自永贞革新以来,财权、兵权、人事权都渐次收归了中央,地方大员割据一方是不可能了,似乎没有封建和战乱了,但是,一方面是地方官员因为无权而无所作为了,另一方面,封建还有没有呢?有的,只是由贵族和地方大员的封建,变成了土豪劣绅和胥吏的封建罢了。这种土豪劣绅和胥吏的封建,“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今为甚者。盖自崇宁极于宣和,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蹇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也就是说,官员们连最肤浅的事都不干,专从事于奔跑进取,“其薄书期会,一切为胥吏之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处。其最骄横者,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户刑,若他曹外路从而效视,又其常情耳。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治理领域,就是办事员的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意思是官员是不断调走的,吏是永远在那里的,宋以来,中国封建的原因就在这些吏。今天有一个词“小官大贪”,说的就是科级以下的权力太大了,因为他是直接办事的。无论你的改革理想多么好,顶层设计得多么完美,但到了基层就推不动了,原因在这里。
毛主席谈到《红楼梦》的时候,他很重视的一回是“痴情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贾雨村为什么听门子的?因为门子说出了《红楼梦》的真谛,就是你要知道你贾雨村是怎么上来的,“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门子就是胥吏,他怀里揣着“升官图”呢。毛主席指出,中国的封建制度就是这样一个官员依赖办事员的制度,因为官员对治国理政这一套是不知道的,他知道的就是走程序,真正办事的是办事员,而不是官员。这样的官吏二分,就造成了所谓“官无封建和吏有封建”的问题。
接下来探讨朱子和陆九渊在宋代的作用。介绍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教规》。
儒家的思想当然不是一个整体,到宋代以后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在朱子手里完成的。他完成的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使儒家深入到了中国的基层。我们知道朱子有很多著作,我讲的是一篇很一般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一般是一般,善璐书记前一段时间让我帮着搞《北京大学章程》,大家找了许多国外大学的章程做参考,我提议去看看《白鹿洞书院教规》,因为这是中国最早的教育章程。
儒家怎么在基层扎下根的?这主要是因为朱子倡导儒家到基层去,把儒家的教条,改造为基层社会的社会行为规范,当这些行为规范为基层百姓自觉遵守,成为他们日用不觉的东西,儒家就成功地立足于中国基层社会,就建立起一整套价值观和价值体系。朱子这种面向中国基层的改革,在中国的政治中是很重要的。
儒家深入基层,关键在于它抓住了一种人,就是父老。当年刘邦取天下,进入长安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与父老约法三章”。项羽兵败垓下,他也说了一句话“无颜面见江东父老”。彭丽媛同志当年唱过一首歌《父老乡亲》。父老是什么?父老就是中国基层的那些乡贤,我们今天所说的乡贤文化,就是朱子首先倡导的。所谓父老,就是今天中国农村的最美乡村教师、最美乡村医生、孝子等等这些人。朱子在中国农村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义学,给没钱的孩子办义学,设义仓、修义渠、修路等等。扶植父老,为的就是他们可以替代胥吏。同时一边教育农村的子弟,一边把基层组织起来去做事。
理学传统的根基是儒家思想的基层化,就是朱子最厉害的一点,比孔子厉害的一点,孔子是鼓励学生都去当官,好比有老师给学生说“你上了北大,竟然没当省部级干部,那就是失败”。我说老师啊,朱子的方向可是与你是反的呢,他是要深入人民群众当中去,做他们的教师,帮助他们办公共事业,这是朱子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在中国基层建立了乡规民约。朱子的这一点,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也最大,日本就是靠朱子学,建立起他们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日本的基层社会,至今还是组织得很好很严密的,这是江户时代以来,运用朱子学治理基层社会的效果。
朱子还有一个贡献,是把王安石的青苗法,改为了社仓法,社仓是朱子的发明,义学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他把国家对于农民的小额信贷,改为立足基层的社会保障体系。他说青苗法与社仓法的区别是:青苗法“其给之也以金而不以谷,其处之也以县而不以乡,其职之也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可见,社仓是基层百姓的互助组织,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里,对于社仓法推崇备至,至于毛泽东呢?我认为,互助组也是受了朱子社仓法的启发。
淳熙五年(1178),朱熹知南康军,也就是到咱们孔总的老家江西星子县做官,在那里建了白鹿洞书院,淳熙八年,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把大家都讲哭了。陆九渊是一个更加讲服务基层的人,他与朱熹的意见有差别,但主张儒家到基层去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北大与大家座谈,鼓励大家读书,引用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就是《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所谓“为学之序”。所以,我说咱们搞大学章程,要看看《白鹿洞书院教规》,这个不错吧?
我前面说,总书记讲治理,不仅仅是讲富国强兵,顶层设计,而是更深刻地讲到社会治理,基层治理,因此方才讲到价值观的问题。他在北大的五四讲话,核心就是价值观问题,关键在于,价值观问题,必须落实到社会规范,特别是基层社会的行为规范。这就是朱子的思想。“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些都是《白鹿洞书院学规》里的话。
到农村去做父老,要像父老对自己的子弟一样去对待乡村的人们,要像老师对待学生一样对待那些子弟。这种价值观,经过很长时间的发酵,在晚清的后期极大的影响了中国的乡间,特别是影响了中国湖南的学者。钱钟书先生的父亲钱基博写过一本书《近百年湖南学风》,他就是讲朱子的思想怎么在湖南的基层得以发展。这个发展最终在曾胡左彭手里焕发出来,怎么做到“朝出鏖兵,暮归讲道,上马杀贼,下马读书”,如何把自己乡里带出来的人叫做子弟兵,大家看曾国藩的家书,也走的是朱子的路。
毛泽东主席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这个思想的影响,人民公社,可以说思想来源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与巴黎公社的原则有关,但实际上,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更与朱子开创的基层互助传统有关,如果一千年来,在中国基层没有这个互助的传统,仅靠巴黎公社的原则它也不成。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实就是把朱子的学说拿来治军,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一套。
如果说“永贞革新”的转化使中国的政治聚焦在财政、司法上,王安石进一步提出了人才的顶层设计的问题,那么朱子之学,这个新儒学,它完成的是中国基层的行为规范、价值观设计,我们今天讲治理,不仅是国家治理,更重要的是社会治理。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很好啊!内政外交,全世界都说好啊,而我们很大的问题在基层、在社会层面、在老百姓的行为规范,这就是全社会的价值观问题。
建立社会规范,建立文明社会,而不仅是富强的国家,靠与西方接轨,靠移植西方的法制,忽视中国的传统和基层,那是办不成事的。因此,我们千万不能说中国基层的老百姓是不懂法的。所谓乡规民约就是中国最基层的法制,存在了上千年了。在这一点上,我又得提一下朱苏力老师,他写过著名的令中文系叹服的文章,《秋菊的困惑》。他分析电影《秋菊打官司》,他说秋菊要的是天理,并不是西方的法。我们一定要知道天理和法制是不同的,法律一定建立在基层的文化和习俗的基础上。离开了文化和习俗,法律是两张皮的,推行不下去的。
《白鹿洞书院学规》这是中国政治的非常好的文献。总书记在北大发表了一篇讲话,讲话涉及到中国历史上许多关于治理的好文章,我们总结中国历史上的治理体系,这些好文章,都应该找来认真读一读,因为这里面有真学问。
接下来要推荐的是王阳明和他的《传习录》,在中唐以来的中国政治史上,王阳明可谓是横空出世。因为他是做事的楷模、行动的楷模、实干的楷模,他也是成事的楷模,无论读书、打仗、治理,他办什么事,就能成什么事,中唐以来,政治家和官员都是文人,是专家型的技术官僚,他们都比较的老实,比较循规蹈矩,有英雄气概、能办真事的很少。与中唐以前贵族化的社会精英不同,宋以来的官员是老实、听话、守规矩而没有能力,与贵族型的治理者比起来,靠考试上来的文人型官员的缺点是不能干事、不会干事、不敢干事,更重要的是:由于选拔任用的程序化、僵化,整个官场和治理队伍的心态和氛围是比较压抑的。而这种灰色的氛围,到了王阳明却为之一改,为之一扫。
![640[2]](/uploads/image/images/d6496871c80047c0a5a9ab9012fd6180.jpg)
我们讲三个自信,在历史上,政治家的自信很少能超过王阳明的。
我们可以把他和柳宗元比较一下。王阳明和柳宗元都曾经被发配到很遥远的边疆,分别发配到广西和贵州去了。官场的失意极大地挫伤了柳宗元,第二次被贬后,他的精神和意志近乎崩溃了,柳宗元曾经写信给他的上司说:有一个人掉在深沟里,他呼号,他抱屈,但没有人听到,听到的人都不理他,或者经过的人,手里也没有绳子,不能搭救他。而恰恰您从这儿走过,您同情我,您手里恰好有绳子,这是最后的机会,您救救我,您把绳子垂下来,你把我从沟里拉上来吧。这种凄惨的呼号表明,柳宗元的意志差不多被官场失意摧毁了,他的精神接近崩溃了,他是比较软弱的,他以为当不了大官、回不到中央,这辈子就完了,其实,韩愈在写《刘子厚墓志铭》时说,如果柳宗元不是官场失意,就不会有那么多锦绣文章留下来了,幸与不幸,这其实很难说呢。
因此,毛主席读到柳宗元的苦诉的时候,每次都感慨:二王八司马是人才,年纪轻轻的不能不给机会。
王阳明恰恰相反。他是个愈挫愈勇的人。他告诉我们说,一个人转移心灵痛苦、精神痛苦的办法,就是去做实事,你做的事越具体、越实际,就越有利于抗拒心灵的痛苦和精神上的失意。这就是他所谓“事上磨练”。而读书人的毛病,就是想得太多,你想得越多,就越畏葸不前,就越心灵痛苦,事上磨练,磨什么?就是通过做事,把你心灵和精神上的那些痛苦磨掉。
因此,他丢官之后的感受,跟柳宗元恰恰相反,他反而很得意,他悟道了,发配边疆,使他看懂了《论语》里的话:。“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他在那个时候写了诗:“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心在夷居何有陋,身虽吏隐未忘忧”,毛泽东就从王阳明那里学到了这种强大的意志力,毛泽东那些豪情万丈的诗,都是在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候写的,《七律·长征》就是这样,毛主席自己说过,环境一好,他反而就写不出诗来了。
我个人非常喜欢王阳明这首诗,什么是自由呢?康德说,自由就是这样一种信仰,就是坚信世界是有规律的,人类的发展是有目的的。一句话,道路是曲折的,而前途是光明的。仅从个人一己的角度看,人生苦短,怎么算计几乎都是亏的,但是,从人类总体角度看,我们都在不自觉的、情不自禁地创造着人类的史诗,都在情不自禁地为他人,为子孙后代做着贡献,这就是人类的天命啊,明白了这一点,就是知天命,就是达到了王阳明所谓的自由、康德所谓的自由。
“却喜官卑得自由”,中唐之后,只有读书人才能做官,读书的目的,就是做官,学而优则仕,白首为功名,社会评价标准只有华山一条路,在这条拥挤的道路上,扭曲异化了多少人啊!这是中国治理史上一个很大的悲剧啊。到了王阳明,他总算把这个事想开了:当官与做事,不是一回事吗。办事非要当官啊?不当官就不办事了?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当官的不办事啊,官越大,就越不办事啊。你不能说,等我做了大官,我才能办大事啊!王阳明就不是这样,他一辈子无论官大官小,活一天,就办一天事。宁肯不做官,他也要做事。王阳明在很高的位置上,几乎到了兵部侍郎的位置上,因为反对刘瑾,被发配到龙场。他到了龙场悟道了,如今我不是中央大员了,我也没啥想法了,这样我就更可以放手办自己想办的事了。
王阳明改变了中国官场的作风,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行动力和强大的意志力,这个人像尼采一样,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面,大家说他狂,首先是因为他敢干。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今天叫做三个自信。怎么解释他的狂呢?王阳明,他一辈子之所以具有高度的自信,就来自他能干事、敢干事,勇于成事,即使被贬到龙场,他也是高度的自信,真是自信到家的一个人。因此,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敢于去作为,敢于去行动。所以他著名的话叫做“知者行之始,行者之成,圣贤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我们说中国的思想影响了日本,第一就是朱子学影响了日本的基层,老百姓都听话守规则,第二个,便是阳明学影响了日本的上层,并与武士道结合在一起,就是上层精英要敢作敢为,不怕牺牲。日本的精英、治理阶层,没有那种见花伤心,见水流泪的士大夫气、头巾气,这就是阳明学的影响。
第二个,王阳明改变了中国官场的作风,改变了治理者的心态,就是他说的“我心光明”。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所谓“阳明心学”的实质。
王阳明深知中国官场的积弊,他看到了治理者心理的健康、精神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一批读书人,挤在这样一条弊端丛生的仕途上,心灵上不扭曲,那才怪呢。整个干部队伍的精神状态,这是治理的大问题啊。这个问题,仅靠填词作赋去派遣是不行的。
他在龙场被贬了五年之后,被重新启用,做都御史,正好赶上朱辰豪叛乱,王阳明几乎是只手平朱辰豪之乱,而且把朱宸濠活捉了。大家都恭贺他,他却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而这就是总书记说的“治世容易治心难”。
所谓扫荡“心腹之寇”,就是扫荡弥漫整个官场、整个治理队伍中的士气低落,精神扭曲,他提出的办法其实简单:大家不要胡思乱想了,不要总是想回中央了,不要心灵痛苦扭曲了,还是集中精力做点事吧,能做多少是多少,做事是实的,其余官帽子大小,那都是虚的,功名利禄是虚的,名声更是虚的。不要沉浸在玄谈玄想里面啦,那只能使你更痛苦,更萎靡不振啊。说白了,这就是他说的“事上磨练”。
还有,要心气平和啊,而怎样才能心气平和呢?他说“天下之人心,皆吾心也”,怎么做到我心光明呢?就是你始终把自己当做天下人,跟天下人始终同心同德就对了,你的心就光明了。他悟道的诗是这样写的:“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尝改。长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缪矣三十年,于今吾始悔。”
王阳明为什么被称为圣人呢?因为他为中国的治理者提供了强大的意志力,中唐以来,中国治理的问题是官员不会做事,是官吏脱节,是上层与基层脱节,这些问题固然都很重要,但是,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是治理队伍士气低落,是治理者丧失了意志,没有精气神,而精气神,是治理的魂,这就是阳明心学,他所谓“养心”所面对的问题。
林林总总,大概给大家汇报上述的内容。这些内容不成体系,但从我这些不成体系的叙述里面,大家一定会感受到,我们中国历史上,是存在一个治理体系的,因此,总书记说我们要系统地总结中国的治理体系,这是他交给我们北大的一个任务,我们一点点地必须做起来,做下去,能做多少做多少,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良好心态,我今天的汇报是粗浅的,不成熟的、点到为止的。今天来了许多专家学者,下面,我想听听真正有学问的诸位的意见。
谢谢!
![640[1]](/uploads/image/images/ac6860df4e4c4398a07934ef08002d0f.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