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未来中国增长主要靠什么?
相关附件:
如今全社会都在热议结构性改革,各行各业也在谈本行业内的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究竟这个概念与我们的生活如何息息相关?北京大学结构性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重点阐明了关于结构性改革几个观点。
与国内许多经济学家不同,林毅夫既目睹了台湾的经济起飞,又亲历内地的改革开放,后来在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师兼副行长时,穿梭于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因此,他对中国的研究始终从全球视野出发,既有对发达经济体透彻的理解,同时又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现状和问题有深刻认识。
“这轮经济下滑主要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造成。”这一观点并非主流,但林毅夫坚信不疑,他通过全球横向的数据对比来说明这一问题。按照这一判断推导政策,他认为,稳增长需要摆在更重要的位置。
近年来,他提了许多对中国经济的灼见,但不少被外界误解。如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可能保持的增长速度的判断、强调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以及产业政策在经济转型升级中的作用等等。在专访中,林毅夫多次提到,“不要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即不能因为政府干预可能失败,就不需要政府发挥作用。
他认为,很多对宏观经济错误的认识被主流经济学所误导,而新结构经济学恰恰是建立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验上的新理论,是对过去发展经济学中的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超越。
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
《21世纪》:你对近年来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速下行一直有不同的认识,认为主要原因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而非内部的体制性因素。
林毅夫:对于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在国内的改革中确实存在许多需要改革的体制性、机制性的因素,但是这轮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引起的。因为从全球来看,无论是发展成熟的新兴经济体,还是高收入经济体,也都普遍出现了经济下行,而且很多国家下行的幅度比中国还要大。比如,巴西201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7.5%,但是2014年只有0.4%。印度也是一个十亿人口以上的大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0.3%,当时我们是10.6%,基本处于同一个水平,但是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4年是7.4%,和我们去年7.3%也差不多,而且印度在2012年改变了gdp的统计方法,从而提升了2个百分点的gdp,如果按照过去的方法,实际只有6%左右,比我们还要低。
再看一些高收入经济体,尤其出口比重比较大的经济体,比如韩国,2010年增长速度是6.5%,2014年也只有3.5%,跌去了一半。台湾地区2014年是10.8%,2014年也只有3.5%,跌去了三分之一。新加坡现在的人均收入接近6万美元,比美国的水平还高,2010年增长速度是15.2%,2014年也只有2.9%,下跌幅度比我们还要大。
这些经济体都出现了普遍的经济下行,而且下滑幅度比我们大,那么总不能说都是我们所讲的体制机制、增长方式的问题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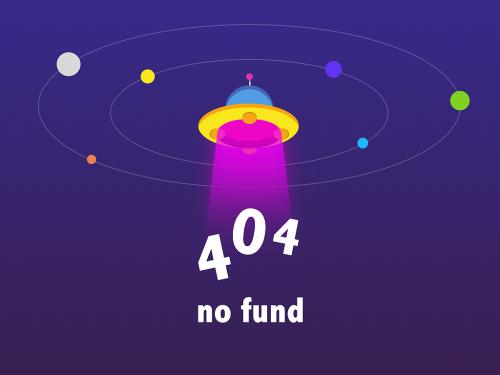
解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的预测中下调了2015年全球经济增速,这主要是发达经济体复苏并不乐观,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明显下滑,甚至俄罗斯、巴西等地区出现了衰颓。在2016年,全球经济与即将出现缓慢复苏,但复苏并不明显,整体经济形势仍然低迷。
《21世纪》:那么,全球经济普遍下行的原因是什么?
林毅夫:美国经济并没有完全复苏,过去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是3%,现在还没有恢复到3%的水平,而且
2016年能不能达到3%也不好说。美国的失业率5.1%虽然与危机前水平相当,但是美国的劳动参与率低了3个百分点左右。因为对劳动者来说,如果一个月不去找工作,就相当于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就不在失业统计里面,但不去找工作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如果把这部分人口计算在内,失业率可能会达到9%、10%,还是高失业率的状况。从2008年到现在,发达经济体还没有进行真正的、必要性的结构性改革。欧洲的情况更不乐观,美国的情况还是要好一些。
从1979年到2014年,中国出口的平均增速是19.4%,但今年前三季度的出口增速却是-1.8%。2008年以后投资建设的项目现在基本上都建成了,但是国际经济并没有恢复,如果没有新的反周期的投资项目的话,投资速度和经济增速当然会下滑。
未来中国增长主要靠什么?
《21世纪》:既然出口已经成为增长的拖累因素,并且未来外部环境大改善的可能性不大,那么中国增长主要靠什么?
林毅夫:从三驾马车来分析的话,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在这两者中哪一个比较重要呢?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投资拉动的,所以现在要转变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我认为,消费确实非常重要,但消费增长的前提是家庭收入不断提高,而收入的提高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靠的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交易费用不断下降都需要投资。有效投资会改善我们的总供给,带来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同时居民的收入水平也会不断提高,这样消费也会提高。过去我们分析宏观经济经常把供给侧和需求侧对立起来,但实际上,两者完全可以统一考虑,也就是现在李克强总理最近在讲的,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投资等同于凯恩斯主义,不能用发达国家的理论来套国内的政策。


解读:
在大宗商品需求和价格出现下降的背景下,不少地区出口遭受重创,不仅仅出现在新兴市场,也出现在发达国家。不少国家为了提振经济和解决本国就业问题,提出制造业回归等政策,这也造成出口压力。
全球经济似乎进入“死循环”,为了突破,多数国家都在进行改革,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以改变目前的增长驱动力。除了改革则是技术创新,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
《21世纪》:未来重要的投资增长的空间在哪里?
林毅夫:总的来说,主要是四个领域: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环保和城镇化。虽然现在我们有不少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比如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等,但都是中低端产业,可以往中高端升级。2014年,我们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就达到1.3万亿美元,这些大多是附加价值较高的产业,这是非常好的投资机会。
这些领域的投资能够提高生产力水平,降低交易费用。这也是我们和发达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发达国家不容易找到高经济回报的投资领域。而且,从负债水平来看,我们的负债率远比一般的发达国家低,民间储蓄、外汇储备规模庞大,因此关键是如何把这些有利的机会结合起来运用,改善我们供给结构和产业结构。这些条件用得好的话,我们达到6.5%以上的经济增长完全有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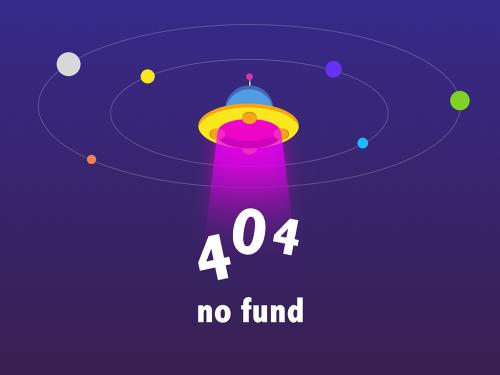
解读:
“十二五”期间,总计奖金万亿元的投资用于治理大气污染;而根据环保部最新的官方说法,“十三五”期间,环保总投资将超过17万亿元。治理投入明显翻倍,我们期待实际效果。
产业政策应主要是降低交易费用
《21世纪》: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了“产业政策要准”,这也是以往没有提过的。在你看来,未来中国的产业政策应该怎么走?
林毅夫:我们现在的人均gdp只有7000多美元,这代表了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异。那么,我们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就还有很多的空间。
我把我们的产业分为五种类型,我们应当根据不同的产业类型施以相应的政策措施:
第一类是处于世界前沿水平的产业,比如家电行业,需要通过自主研发进行产品技术创新,以保持世界领先。第二类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这些领域的优势已逐渐丧失,绝大多数加工企业可能要转移到海外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区去设厂,将gdp变成gnp。少数企业要转向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打造品牌,并加强对研发的投入。一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在其他国家需求还很好,也需要帮忙转移出去。第三类是处于追赶阶段的传统产业,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异依然很大,可以继续采取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战略。第四类是手机、互联网等新产业,研发周期特别短,资金需求不多,可以采取弯道超车的办法,利用我国的优势,与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第五类是资本投入特别大、研发周期非常长,且关系到国防安全的战略产业,需要政府财政直接提供支持。
《21世纪》:中国的产业政策经常会出现中央一鼓励、地方一窝蜂的重复建设情况,而且很多是为了获得政府的补贴。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林毅夫:我谈的是产业政策从来不谈补贴,我谈的是因势利导。政府要做的是降低交易费用,如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培育、金融环境和法治环境改善。如何避免一窝蜂的现象出现呢?首先,各种要素价格要反映要素的稀缺性,这才能反映比较优势所在。第二点就是对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给予外部性补偿。
政府为什么要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外部补偿呢?因为一般发达国家都有比较好的专利保护,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很好的专利保护,因为它还处于技术引进和吸收的过程之中。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如果企业创新成功了,也没有垄断利润,很多模仿者就会跟进来,成功的好处大家共享。但是失败的话,风险就全是自己的。但是如果没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怎么有产业升级呢?我们看到,没有一个成功的国家没有政府的因势利导。华盛顿共识以后,拉美最成功的国家是智利,但是智利有三十年没有新的产业,因为没有新的产业,劳动生产率没法提高,劳动者收入也没办法得到提高。
我提的给予外部性补偿也就是几减几免而已,这种补偿是在企业有盈利以后,对公司所得税的优惠,这是相当有限的,除此之外并没有金融的补贴。
政府干预确实可能造成失败,但不能说因为政府干预有失败,就不要政府,这是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因为如果政府不发挥作用,就必然会失败。
(本文选自《解题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大棋局》,原文名为《林毅夫:供给侧和需求侧应统一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