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专业经济学家中的天才人物
相关附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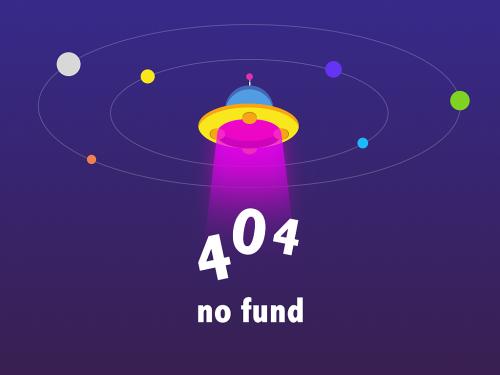
肯尼斯·阿罗在北大国发院做讲座
虽然活了90多年,肯尼斯·阿罗(kenneth joseph arrow)辞世的消息仍令人感觉“意外”。这位90岁生日研讨会上被誉为“校园里最后一位文艺复兴式人物”的学者,瘦小身躯承载着一颗巨大头脑,在斯坦福校园里骑着自行车,随时可能停下来与熟人或学生讨论任何问题——从潜水艇声呐技术到奥巴马医改问题,72岁发表“知识理论”工作文稿,88岁访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建议重新考虑国民财富的计量方法——将人力资本和知识存量的服务流与资源环境的耗竭纳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由此催生的世界银行2011年“各国财富变迁”报告专向阿罗致敬。我在香港大学任教期间,偶然与张五常谈起阿罗的头脑,五常教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张五常为听众讲解了“交易费用”理论。会议结束,在走廊里,阿罗递给他一张写满数学公式的小纸片,说:你刚才讲的内容都在这里。
手机短语“活久见”,原意是“活得久了什么奇怪的事情都可以见到”,我的转注是:见识随年龄增加而丰富,逐渐化为智慧。当然,这样的“转识成智”过程还需要与特定的头脑结合,才可理解阿罗的思维方式。根据哈耶克描述过的两类头脑——混沌型的和清晰型的,显然,阿罗的头脑是清晰型的。事实上,在我考察过的第一批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当中,萨缪尔森与阿罗都有清晰型头脑,再加上他们已得到承认的天才——拉丁文“天才”这一语词泛指每一个人都有的使人之所以为“人”的潜质,于是他们成为我视野里“专业经济学家”群体仅有的两位天才人物。仅有的,因为另一位天才人物,小密尔,出现于19世纪上半叶,那时尚未出现“专业经济学家”这一群体。哈耶克的头脑,他自认是混沌型的。我在另一短文(“涌现秩序的表达困境”)里论证过,清晰的表达是有代价的。思想的最深涵义因为不可表达于是往往被表达遮蔽。我们每一个人真正重要的感受,被逻辑学家金岳霖称为“真”,就此而言是不可表达的。或者说,“真”的命运就是被表达遮蔽。所以,金岳霖说过(《知识论》),倘若“真”与“通”不可兼得,他宁可求其真。
我记得萨缪尔森1998年在mit经济系走廊尽头他的办公室里见到我时,首先提醒我说他是“最后一位通才”(the last generalist),最后提醒我不要忘记让他站在办公室那块黑板前拍照。虽然,拍照效果很差,我仍记得他在黑板上临时写的数学公式是曲面上的多重积分——萨缪尔森文集里有一篇短论的标题是“经济学与熵”。在谈话中他提到mit经济系另一位天才戴蒙德——peter diamond,2010年(萨缪尔森2009年辞世)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用的是“genius”这一语词,而不用“通才”这一语词。事实上,戴蒙德做的工作大约可得两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却仍不算“通才”。萨缪尔森和阿罗做过的工作,我粗略判断,大约每位都可得四个诺贝尔经济学奖。
与萨缪尔森的富裕家境恰成对照,阿罗的家境完全称不上富裕,甚至,他晚年回忆时自称“家贫”。如果我们想象将人们的头脑依照潜在重要性分布在“先天重要性”的横轴上,按照通常可接受的假设,这是一条正态分布曲线,它的峰值对应于多数人的头脑(样本),峰值右侧稀疏分布着少数逐渐被称为天才的头脑,峰值左侧则分布着少数被认为愚笨的头脑。社会制度之所以重要,因为峰值及其右侧的头脑的潜在重要性,仅当它们从特定社会制度获得足够资源时,才可实现自己的重要性。虽常被扼杀,天才头脑仍按“幂律”描述的万分之一概率降生于人世间,在正态分布峰值的右侧——不论家境贫寒还是富裕。顺便论述,基于常识,在峰值右侧的头脑,投生于贫寒家境的必定比投生于富裕家境的多得多。所以,行为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是:怎样的社会制度可使峰值右侧贫寒家庭的头脑的潜在重要性不被扼杀?并且由于愚笨的头脑远比天才的头脑更容易生存,当我们观察任一社会(先天与后天交互作用之后)的头脑的分布曲线时,在峰值左侧的头脑似乎远比峰值右侧的多,更像是有一条左侧的“肥尾”。这是我2017年即将发表的新作主题,此处不赘。
阿罗家境贫寒,头脑天才,于是读可以读到的任何书。富家子弟则常因“可选集合”过于丰富而丧失了读书的欲望。然后,根据阿罗晚年自述,他偶然拿到的一本数学书是抽象代数(也被数学史家称为“近世代数”)。此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服役期间,他尝试并放弃了若干博士论文选题,直到被“半序结构”灵感击中,写了“阿罗不可能定理”初稿(强化的版本可表述为:两议题以上可选议题集合上的至少包含两人的集体选择过程关于满足“完备理性 全域可变偏好 非独裁 弱帕累托原则 无关议题独立性假设”的不可能性定理)。据阿罗回忆,在学术报告现场有一位加拿大数学家,以关于民主的充分必要条件“四要素”(关于两议题的简单多数民主原则=决断性 议案中性 投票者中性 集体决策对投票者意向变动的非逆向变动性)而闻名于世的“梅定理”(may theorem)的作者(kenneth may)。梅的定理,被最著名的经济学期刊拒稿两次,不如阿罗定理这样幸运。由“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引发的,是一大批“不可能性定理”,数量之多,恰如布坎南最初对阿罗定理的严厉批评所言,遮蔽了真正重要的问题意识。到了1980年代末期,几份最重要的学术期刊不再愿意发表几乎每月都涌现出来的“不可能性定理”——迟至2016年9月我检索“万方数据”学术服务器时仍可见到国内学者发表的不可能性定理。森(amartya sen)在1990年代的一次演讲,开篇即表明态度:在每一个不可能性定理的附近必定可以找到许多“可能性定理”。森1970年证明了“满足最小自由的帕累托效率之不可能性”定理,二十年之后他表明的这一态度,足以警醒学界,不可仅仅根据逻辑框架内的各种不可能性定理就简单否定现实世界里的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专有一节批评森的不可能定理,由此引出森与诺齐克之间的一番论辩,寓意深远,至今余绪不绝。在远比阿罗完备理性两项公理所要求的“传递性”假设弱得多的“拟传递性”假设下,森证明了社会选择的一般可能性定理。事实上,阿罗定理的上列五项假设在任一方向上的弱化总可导致社会选择的可能性定理。
不论如何,阿罗的博士论文“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以及他为我的学生丁建峰撰写的这篇论文的中译本前言),值得每一位当代的社会科学家特别是研究中国转型期社会大范围制度变迁的学者继续研读。诺贝尔委员会授予阿罗和希克斯1972年的经济学奖,主要因为他和希克斯对“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的贡献。斯密“看不见的手”经济学研究范式(自利的人、完全私有产权、信息无成本,则“自由市场”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等待近两百年,在拓扑学的“不动点定理”被发现之后,才获得了逻辑基础。由伯劳威尔不动点定理(有界紧致集到自身的连续映射必有不动点)扩展而得到的角谷不动点定理(将“连续性”弱化为“上半连续性”于是“不动点”扩展为“不动点集”),被纳什用来证明n 人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的存在性,也被阿罗和德布鲁用来证明(在若干技术性假设下)斯密范式里“全部市场出清”的自然状态(又称为“一般均衡”的价与量)的存在性定理。稍后,阿罗和德布鲁证明“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在完全私有产权的制度安排下,这样的一般均衡满足帕累托效率原则(即没有人可能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福利并且不降低任何他人的福利),以及完全属于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存在“初始产权”的分配使一般均衡满足预先指定的社会福利状态)。这是政治经济学议题,因为,为满足预先指定的理想状态而必须有的产权关系调整,很可能意味着“社会革命”——例如剥夺“剥夺者”。
根据阿罗的自述,在1972年之后,他的学术兴趣越出了诺贝尔委员会授予他经济学奖时所说的范围。新的兴趣集注于知识生产与信息经济学议题,并导致了阿罗的“最佳科层”理论(成为任何信息不完备条件下“组织”设计的基础),和阿罗的不确定性经济学——医疗、保险、知识探索。
其实,阿罗的第四贡献是“收益递增的经济学”。篇幅有限,我在《经济学思想史讲义》里提供了这一学说的详细脉络,并且在《行为经济学讲义》里提供了社会网络收益递增研究状况综述。概而言之,在互联网时代,经济学如果还有未来,它必须是关于几乎无处不在的“收益递增”效应的经济学。
回顾阿罗的思想历程,使我感慨颇多的是,假如阿罗的天才头脑因贫困而读的数学书不是抽象代数而是数学分析,后来的经济学思想史很可能改写。萨缪尔森的博士论文“经济分析基础”,恰如标题所示,为现代经济分析奠定的了数理基础——基于实数的连续性假设以及实函数的可微性假设。但是,制度变迁不连续。从一套制度(可定义为相互之间足够强烈互补的行为规则的集合)到另一套制度,更经常发生的是“断裂”。至今,演化社会理论还很难提供制度变迁的演化逻辑(就连“演化”与“逻辑”这两个词的联用都是悖论性的)。
可是,中国社会晚近几十年乃至百多年间发生的大范围制度变迁,确实提供了难得的素材。例如,我的感受是,不论建构怎样普适的逻辑框架,这一框架必须容纳的一项基本事实是,特定社会的制度变迁表现出强烈的路径依赖性。基于常识,中国制度变迁哪怕延续几百年也不会并入美国、德国、日本、越南、新加坡、俄罗斯、印度、马来西亚以及任何其他社会的制度演化路径。这就意味着,如果我可以将制度分解为要素的集合,那么,这一集合上必可定义某种代数运算,它使任意两项制度要素的相互作用仍在这一集合之内(封闭性)。换句话说,制度变迁可能表达为“半群”的代数学,如果更理想,也可能表达为“群论”。我读阿罗的时候,在深层问题意识引导下,更常思考中国社会的大范围制度变迁。幸亏他当时读了那本代数书,现在他引导我思考制度变迁的代数学。
在阿罗使用代数工具研究社会选择过程之前,1934年,熊彼特带着一份未完手稿,登船前往哈佛任教。遗失多年之后,2005年,这份手稿发表于著名的经济文献杂志。熊彼特在这篇文稿里拒绝承认自己早年(1911年)成名作品“经济发展理论”确立的企业家创新原理,因为,他意识到,当新观念从旧世界涌现出来的时候,新的世界“突然”取代了旧的世界。他使用的语词(参阅汪丁丁2014年《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恰好是“discontinuity”(不连续性)。
阿罗突然走了,他在我的世界里激活的思绪,不能随之而去。
本文刊于《财新周刊》
文 | 汪丁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