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再谈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相关附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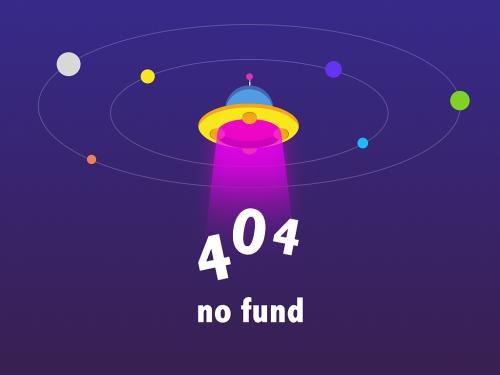
《经济的限度》
汪丁丁 著
中国计划出版社
2017年8月
感谢徐晓和她的编辑团队至少两年来的不懈努力,这本“文选”(选自2010年以来我写的文章)终于出版。我撰写这篇序言时,有机会重温这组文稿,并惊讶地发现它们被编辑重新安排之后简直可说是“焕然一新”。这本新书的序,我认为,最合适的标题是“再谈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事实上,我在以往三十多年里写了不少文章探讨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收录在这本书里的文章,至少两篇以此为主题。其一是2014年我在杭州湖畔居与周濂的长篇对话,另一篇的标题是《复杂思维为何艰难》,也是2014年写的——那一年中国与世界的学术界受到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思想冲击,为此,我写了一组文章,收入张进主编的《中国改革》。张进在财新网发表的评论中特别列出他理解的我这组文章的关键词:中国奇迹”“收入正义”“资本财富”“复杂思维”。读者不难在这本书里找到以这些关键词为标题的文章——《中国奇迹的历史与未来》《收入分配与正义诉求》《资本与财富》,以及上述两篇关于复杂性的文章。与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密切相关的,是这本书里其他文章的主题,例如我为阿瑟《技术的本质》2014年中译本撰写的序言,在财新网发表时的标题是《锁死的路径》。又例如《互联与深思》《人类创造性的两大前提》《互替与互补》《竞争与合作》《自由与自律》。逐渐地,读者不难理解这组文章的基本方向,那就是借着探究中国问题的复杂性,经济学理论或许能够超越以往的局限性。例如,这本书里有两篇这样的文章:《美食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基本问题》。
以往的经济学理论,核心议题是“稀缺性”——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因为“稀缺”所以“竞争”,或者,当我们观测到“竞争”时,我们可以推断“稀缺”。所谓“新制度经济学”或“产权学派”经济学,核心议题是竞争稀缺资源时不可避免要有的各种“歧视”标准的孰优孰劣之分析。于是,经济学关于稀缺与竞争的理论,从个体的理性选择扩展至群体的决策行为。如果群体人数很少,那么,经济学家更愿意运用“博弈论”方法于群体行为。不过,当群体人数众多时,博弈论并不是好用的分析方法。例如,当我们分析中国“转型期”各种社会制度孰优孰劣的时候,由于群体人数众多,群体成员相互之间行为预期的不确定性成为任何理性选择模型的主导因素。注意,这里出现的是奈特在百年前考察的那种不确定性——特指那些不可重复从而不可预期“事件”,它们当中意义重大的,现在被称为“黑天鹅事件”。这种不确定性无法被假设“信息完备”或“信息完全”的博弈理论容纳,尤其是,应对这种不确定性的理性选择模型不再可能如以往的博弈分析那样是“逆向推演”的。取而代之的是,例如“基于案例的决策理论”(也称为“基于以往经验之间相似性的非贝叶斯决策理论”),又例如来自统计物理学的随机过程分析方法(出现在宏观经济学教材里的版本是“动态随机过程一般均衡”方法)。但是经济学家在引入这两种新方法之后,几乎立即意识到伴随新方法的核心议题——“复杂性”,或任何复杂系统的“非各态历经”演化特征。典型的各态历经,就是布朗运动的特征——假以时日,空间内的简单布朗运动可以达到任一位置。可是,复杂系统的特征在于,它以往的演化改变着它现在的结构于是很可能永远无法达到某些位置,所谓“非各态历经”演化特征。在这样的“演化社会理论”视角下,如果这些永远无法达到的位置的集合包含着各种被称为“均衡”的状态,那么,社会系统的复杂性意味着社会演化可能达到另外一些状态,例如“崩溃”或“解体”。
其实,我写的中国文章,问题意识当中始终有上述复杂性的牵挂。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喜欢和乘客攀谈,而且喜欢发表政经评论。在以往五年里,我遇到至少三位这样的司机,非常不满意“邓小平时代”的市场化改革。他们的不满,我这样概括:当初的口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这些富起来的人却“为富不仁”(当然还要“官商勾结”)垄断了全部经济资源,致使中国社会再度出现了“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我的这一概括,可追溯至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公认的老师奈特在1930年代为学生们讲授微观经济学时的“开场白”,他提醒学生们,首先,不要以为世界上有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其次,完全不受社会制约的自由竞争很可能导致财富积累和权力垄断到完全消灭自由的程度。阿罗是奈特的学生,以“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以及相关的理论贡献而获诺奖。但是我认为诺奖委员会忽视了阿罗的另一个“不可能性定理”,这一定理可以表述为:不可能有包含全部社会系统在内的自由市场。换句话说,只能有嵌入于既定社会之内的市场经济而不能有嵌入于市场经济的良序社会。
出租车司机们的不满,根据我的上述概括,表现了社会演化的“复杂性”:当初的市场化改革获得中国社会大多数人的积极响应,由于市场化化改革而形成的新的社会结构逐渐改变了大多数中国人对市场化改革的态度,新的态度凸显为公众对最近十几年“反腐败运动”的全面支持(包括使权力集中于领导反腐败运动的核心人物的政治支持),这一集权过程又倾向于成为对改革初期“放权让利”过程的完全反动,甚至,为强化这一集权过程而采取的“意识形态”,逻辑地要求批判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政策,以致最热衷的改革者们不再相信改革是“不可逆转的”(即承认存在着一些中国社会永远不可达到的状态)。
一如既往,我是悲观主义者。在演化社会理论的视角下,中国转型期社会的未来从来就是不确定的,并且这种奈特意义的不确定性逻辑地意味着复杂性和“非各态历经”演化特征。我写的这篇“序言”,本质上是这本文选的“升级版”,仅仅为早已读懂了这本文选的读者而写。我的长期读者从来就知道为理解我现在的文章,他们通常必须回溯我以往几十年发表的文章。不如此,就不能“升级”。
文章转自财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