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观察》访谈周其仁:怎样理解80年代和专车
相关附件:
【上观年度访谈】周其仁说,长期研究农村问题,但农村的钥匙在城市,而要研究大城市,国内还有哪个比上海更典型?
前几天,在新天地随便找了家咖啡馆,约的是能见度颇高的经济学家周其仁。那天上午,他刚从北京飞来上海,中午见一位朋友。下午两点半准时赴约,见面就抱歉,说一会儿还有个安排。
当时有点担心采访效果。没想到一聊就聊了两个半小时,年过花甲的周其仁始终专注而有激情。一直到我提醒他是否要赴下个约了,他才看了下手机说:“真得赶紧走了。”然后又说:“不好意思,还得让您埋单。”
周其仁有多重身份。称他是顶级经济学家,他说都是被时代推着走的,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有多大本事;说他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创院院长,他说根本做不来行政工作,事情都是别人做的。问他如何自我定位,他说自己是个老师,也是个经验主义者。
在周其仁看来,每次来上海都是探亲。因为他生在上海,而且母亲至今生活在此。但很明显,他的上海话已经生疏,只是偶尔会蹦出一两个上海话单词。他长到18岁,第一次离开上海。40多年后,受聘担任上海决咨委专家。他说,长期研究农村问题,但农村的钥匙在城市,而要研究大城市,国内还有哪个比上海更典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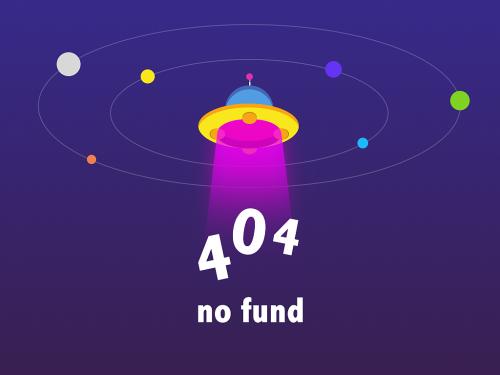
【人物档案】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前任院长,经济学家。2010-2012年,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1950年生于上海。1968年至1978年,东北农场插队落户。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之后相继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工作,从事改革与发展问题的经济研究。从1989年到1991年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访问。1991年秋就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后获经济学博士学位。自1996年起,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
研究领域侧重产权与合约、经济制度变迁、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与管制、土地制度改革和城市化、货币与金融等方面。
我们都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那个时代让人怀念
高渊:杜润生先生最近去世了。曾有人说你们不过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但你回应:“此生以此为荣。”你当年在杜老领导下工作,觉得他身上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
周其仁: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高考来到北京的。当时因为提倡解放思想,北京处于一种非常活跃的思想状态中,有各种各样的沙龙、讨论会、读书小组等。我参加了一个读书小组,里面有一位是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资料室的老师。有一次他说有位老人愿意见你们,谁有兴趣去见,就这样见到了杜老。
那时候有一帮大学生,都常去杜老那儿。他态度和蔼,鼓励年轻人在他面前畅所欲言。老头不会批评你,就是问问题,鼓励两句,所以谈得很开心。
高渊:他喜欢跟你们谈什么?
周其仁:年轻人关心的他都有兴趣。1979年我们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复出,当了国家农委副主任。但看上去很悠闲,不是绷得紧紧的,似乎总有大把的时间跟你们聊。在我的印象中,他很有自己的看法,但不会强加给你,而是会引导你。
我读的是经济系,连着几个暑假都参加农村调查,就放弃考研了,一头扎进去,从此没有回头。这跟杜老有直接关系。他有兴趣听年轻人不成熟的汇报,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建议什么,批评什么,他给了很多机会。他的插话、提问,就像导师一样,会让你自己知道几斤几两。我们谈着谈着就知道自己功夫不行。但有冲动,还想回去再把事情搞清楚。
当时和他聊得比较多的,除了我们人大的,还有北大、北师大和北京经济学院的同学。我们大多下乡好几年,觉得农村现状很难改变,好像天生就是这么穷。但1980年前后的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给了我们鼓舞,说明如果想法对头,能够深入调查研究,能够从底层吸取力量,能够制定正确的政策,是有可能推动农村变革的。
1982年,我大学毕业,和陈锡文、杜鹰、白南生、高小蒙他们一起,被分配到杜润生门下。当时编制设在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办公地点在西直门内半壁街,调查研究工作则由杜润生领导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直接领导。
高渊:1986年,杜润生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成立农村发展所,王岐山和陈锡文先后担任所长,都当过你的领导。你对他们有什么印象?
周其仁:王岐山真是没话讲。我们搞研究的人,个性上多多少少有些毛病,但他都能团结起来,让大家往一个目标走。后来他有这么大的成就,是有道理的。
陈锡文是上海人,到黑龙江下乡10年,多年后一直当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有人说,怎么弄个上海人来管农村?其实他长得就像农民,黑黑的,非常朴实,学的专业就是农业经济。这些年,他在那个位置上,大家给他的压力也不小。当然,学界呼吁的农村改革,有些也不见得马上就可行。他的位置不一样,我老说中央就是得站在中央,不能冲在太前头,否则翻了车没法收拾。
高渊:今年以来,万里、杜润生等人陆续故去,很多人感叹80年代改革先驱一代已经告别。他们那一代人为何有这么充沛的改革激情?
周其仁:那是因为中国被逼到墙角了。如果没有“文革”,没有以前极左的错误,也很难有那么一场改革。杜老是智囊型人物。上面有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人,那是决策层,杜老是帮助决策、提供思路、参与决策。这很重要,因为完全可能提供不同的东西。
万里是大将风度,他话不多,理论也不多,但真有风浪来的时候,他可以顶住。杜老很柔韧,能够汇集不同的意见,把原来完全对立的东西缝在一起,这样让中央做决定的时候可以减少阻力。
现在有人说杜老是“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其实他要说服很多人,汇集很多人的正确意见。对于大国改革来说,这个环节很重要。很多事情,就是因为真实情况搞不清楚,高层再有勇气也难以拍板,或者拍了也落实不下去。所以要把情况弄清楚,再加上政治智慧和勇气,缺一不可,才能解决问题。所以,80年代还是挺令人怀念的。
不必人人操心天下大事,但加起来要让社会往前走
高渊:很多人说,现在的人天天埋头挣钱,更多关注个人生活。你觉得,当年那种情怀还能找回来吗?
周其仁:这是难以避免的。说实话,从社会发展来看,如果所有人都天天操心天下大事,也不见得一定是好事。所谓好的市场经济,就是每个主体为自己谋利,通过为别人、为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谋得自己的利益。这样加起来,经济社会就向前发展了。
当年的改革,是要把市场的门打开,而这门真打开了,就是这么世俗的画面。80年代是破冰之旅。如果现在的人不把自己的专业琢磨得透彻一点,天天讨论国家大事也有问题。当然在情感上,人们会怀念当年的英雄情怀。像我们毕业的时候,觉得研究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农民进城真有意思,我们赞赏那个时代的精神状态。但也要理性分析,那是一种非常态,难以持久的。
高渊:不少80后说,现在整个社会阶层逐步固化,即便努力了,但被固定在某个层面的现实很难改变。你怎么看这种情绪?
周其仁:所谓固化,是不是说社会更有秩序了?这方面看也有积极意义。如果天天变来变去,恐怕有问题。现代化的过程,在马克思·韦伯看来,官僚化有一定的正面意义,当然我们要担心不能把这个变量搞得太硬了。我们这个时代突破固化的关键,还是依靠新技术、新组织。你看马化腾和马云,他们能够冲出来,从这个角度看并不固化,因为过去所有的产业界大佬或社会精英在他们面前都黯然失色。
创新不光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发生变化,也提供了突破社会关系固化的机会。只要开放,只要新技术处于机遇期,一切都有可能。像马云念的学校不算好,但他不也冲出来了吗?
高渊:现在都在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是社会变革创新的最佳渠道吗?
周其仁:这个口号的积极意义,是能创造一种积极的氛围。现在再保守的人,也知道政府在倡导创新。你说创新,人家就不好意思一棍子打回去,这个作用很重要。最好的情况是,即使我自己不能创新,也要支持别人创新,希望能达到这个效果。
当然,最终能创新成功的,总归是少数人。我有一次去以色列,问一起去的中国企业家,这几天看到什么新东西?他们都说没啥不一样,多数人的生活方式跟我们差不多。但为什么以色列的创新做得好,可能就是他们中千分之几的人的状态跟我们这里非常不一样。
一个发明创新一旦应用,所有人都可以分享。这也是上海要关注的问题。我们强调公平很重要,但科研要有适当倾斜,因为爱因斯坦只有一个。保护多数人和关照少数人,是一门艺术。优秀的人冒出来,会改善其他人的状况,在分配当中,就要让有些人享受很多资源。如果大家都一样,必然平庸化。
顾问上海是天赐良机,但若只是开会我不会来
高渊:2013年开始,你担任新一届上海市决咨委专家。为何接受这份聘书,因为是上海人吗?
周其仁:更多是因为我长年研究农村问题,包括农村工业化、城市化。我们国家工业化的成绩不错,把很多剩余劳动力都从农村带出来了,但城市化现在遇到不小的挑战。现在农业产值占gdp的10%左右,像上海是0.5%,江苏是6%,广东是5%,这是反映现代化进程的。工业发展起来,农业在gdp中的比例肯定低。
但是你看农村,现在待在农村的人是多还是少?很多人说农村没有什么人了,这是观察力不够才会得出的结论。我们要思考,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村庄?你看东亚所有高速发展的经济体,工业化在推进,城市化在推进,人口在移动,村庄数量会迅速减少。通过土地整理,很多地方都恢复为耕地和绿地了。
我们这方面是滞后的。现在全国还有近60万个行政村,按一个行政村有10个自然村算,那就有600万个自然村。每个村出来一些人,稀稀拉拉留下一些人,这些村庄的生活就缺乏活力,因为人气都没有了。接下来的重点,还要推动很多农村的人出来,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产出占百分之几,劳动力也占百分之几,这样至少农业劳动力能得到中国劳动力的平均收入。这个问题就是杜老到90岁还讲的:让更多的农民转出来。
高渊:所以你把目光转向城市,因为农村的解药在城市?
周其仁:现在的情况是,人人都要去的地方,承载能力不行,人仰马翻;大家不要去的地方,在大建大修,最后不知怎么收场,全是债务。所以我想,我们研究农村的人也要好好研究城市,看看这个局怎么破。
2013年,上海请我当决咨委专家,对我来说是天赐良机,因为我正好想转向城市研究,而上海是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具有极强的典型性。我对上海决咨委办公室的领导说,如果请我来就是开几个会、讲几句话,那就不需要来了,因为我并没有发言权。如果有机会做些深入的观察和研究,那还比较有意思。他们一口答应了。
高渊:你对上海的研究,从什么点切入?
周其仁:我在研究城市化方面,有一些积累,可以运用到这里。城市的“市”就是市场的市。上海是高端市场,所以这两年我把上海的交易所全跑了一遍,了解它们的来龙去脉。这是一个切入点。
所谓中心城市,就是要给很大一片区域提供服务。我曾在纽约泡过一段时间。为什么纽约是全球城市,因为它提供的辐射和服务是覆盖全球的。全世界很多企业,包括我们的阿里巴巴要上市,要跑到纽约去。什么叫纽约?就是你有巨大的野心和想法,但你缺钱,那就去纽约吧,到纽约就可能圆梦。对上海来说也是这样,关键是中国内地省市甚至是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它缺什么东西,就可以到上海来寻求帮助。能否做到这一点很重要。
第二个维度,就是科创中心建设。上海究竟要产出什么东西,这也是我们调研的重点。上海集聚了这么多的高校、科研院所,产生多少“想法”?传到了多远的地方?我特别感兴趣什么东西是上海人创新的,并辐射到外面去了。
还有一个维度是文化。听说外国游客谈到对上海的印象时,很多人表示喜欢一部叫《时空之旅》的多媒体剧。这部戏在上海已经演了很多年。其实成功的演出就是一个城市的一个吸引因子。纽约的百老汇就有这个功能,很多人一家老少去纽约,看一场演出就走了。在这方面,我们还差得很远。文化是一种重要的城市吸引力,非常值得研究。
慢慢地,我形成了一个研究上海的思路:辐射力怎么样?吸引力怎么样?承载力怎么样?现在主要围绕这三个维度做访问调查。
高渊:你每次到上海来,是不是要开个调研菜单?
周其仁:我跟决咨委办公室的年轻人一起商量,因为他们对上海比我熟。我希望利用这段时间多学点东西,毕竟城市比农村复杂得多,但研究方法是一样的,就是经验主义的办法。先接触现象,提出一些问题,然后顺藤摸瓜。
高渊:担任这个角色已经两年多了,对上海有什么新认识?
周其仁:近代以来,上海为什么发展这么快?道理很简单。上海不是管出来的,而是放出来的。
中国最早出现路灯的城市就是上海。上海以前也没有路灯,谁上街谁自己点灯。穷人摸黑,富豪点个大灯,都是自备的。后来因为华洋杂居,把欧洲的理念带过来。上海决定由市政出资建路灯,当时是煤油灯。没想到夜市随之发展起来,这是革命性的。当时还有很多官老爷观念转过不来,说为什么要在马路上给别人点灯?当时上海是工部局体制,他们发现了问题,研究了问题,自己筹资就可以解决问题。
今天的上海同样如此。一定要敢于先行先试,不能等着别的地方做了再做。这样的话,一是机遇失去了,二是不符合上海在全国的定位。
专车思路可破解大城市死结,意义不亚于当年农村改革
高渊:说到这里,就必须提一下网络专车了。今年10月初,上海向专车平台发资质许可,这在全国甚至全球都是创新之举。同时,还接纳“优步”进入自贸区。受到关注的同时,也引来一些争议,你的态度如何?
周其仁:这其实和当年马车被出租车替代是一个道理,它的合理性是必然的。当然,一定要处理好新旧矛盾。现在“分享经济”刚露头,大势不可阻挡,争论必定纷繁。
大城市管理一大难点就是道路。第一,道路增速永远赶不上车辆增长;第二,城市道路在时间上始终是不平均的,高峰的时候堵得一塌糊涂,半夜都是空的。现在破解这个矛盾的天赐良机就是专车。专车看起来是私车,其实是公共利用,而且如果给它们以适当的法律环境,引导好这种公共利用,就有可能抑制人们买私车的冲动,或者买了私车也减少上路。
我一直向有关部委建议,不妨让各个城市试验一把。不是一定行,也不是一定不行,因为出租车管理不是全国性业务,不是国家事权,说到底是市长们的事。有些地方试验下来效果好的,也可以供其他地方参考。
我自己认为是有可能行的。为什么很多旅游景点周边有家庭旅馆,就是因为季节差。旺季宾馆供不应求,淡季门口罗雀。这就需要发展“分享经济”了。
高渊:很多人说,高峰的时候专车出来不是更堵了吗?
周其仁:其实市场会调节。太堵的话,专车司机赚不到钱,但好就好在他不是全职,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在空中”讨价还价。
我有一次在国外用“优步”,它会告诉你,这个时候是高峰时段,价格比平时高,你要不要?如果要,专车就来。传统出租车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如果允许拦着出租车当街讨价还价,交通就瘫痪了。这说明发挥价格机能要讲条件。现在的互联网技术提供了可以利用价格机制的条件,再拒绝就没道理了。
从这个思路看,专车极可能是破解城市交通承载力死结的突破口。现在还有一个新东西,就是“空中酒店”。我最近去首尔开会,他们请了这个创始人去做分享,就是一个美国大男孩,大学毕业没几年,现在手里有遍布全球的200万间房间随时提供出租。
我们的城市膨胀得这么快,盖了这么多房子,能不能分享利用?我有一次讲,上海有多少洗衣机,占了多少地方,按上海的房价算,那是多大的资产啊。为什么每家都要买洗衣机?能不能通过某个信息平台实现共享?这就是“分享经济”。它带来的变革意义,一点不亚于当年的农村改革。
高渊:在你看来,现在的专车就是当年的包产到户?
周其仁:本质上是一样的,都会带来革命性变革。当年农村包产到户是怎么起来的?就是被逼到没办法了,民间拼死尝试,社会几多争议,高层默许一试,最后点头推广。
专车管理有上海市交通委冲在前面尝试,是天降的大好事。怕的是没人愿冒风险啊。所以,破解社会难题的答案,不在书斋里,而是在实践中。
高渊:放在前几年,极少有人能预见到会出现专车,并且发展得这么快。你觉得从专车现象来看,对我们制定“十三五”规划有什么启示?
周其仁:前一段,我参与全国和地方层面的“十三五”规划讨论。我提醒过一句,我们要看看当年制定“十二五”规划时,有什么事情没有预见到。我觉得至少有两件事,一是互联网发展得那么快,二是经济下行压力比预期的大。
我们要承认,当今世界科技进步越来越快,总有些事情我们事先预见不到。在制定“十三五”规划时,要为目前看不到的事情留有足够的空间。在产业发展方面,我始终认为不要以为能够指哪儿打哪儿。最好留点机动去捕捉今天还看不到的机会,对付今天还看不到的危险。还有很多事情要敢于尝试、敢于探索,上海就应该是探索者的角色,要在全国冒尖。
把自己当成外星人,看地球人被卡在什么地方了
高渊:你生在上海,18岁时去了北大荒。如果当年留在上海,人生轨迹可能跟现在不一样吧?
周其仁:我小时候家住愚园路,中学毕业遇到文革,然后毛主席一挥手就下乡了。坐了4天3晚火车去了黑龙江,当时是主动报名的,真是热血沸腾。很多同学都留在上海。我们当时挺理想主义,看到北京学生已到内蒙插队,很着急,坚决要求下乡。因为家庭成分关系,当时兵团来招人还挑不上,那年我们中学一共12个人去黑龙江,我排在最后一个,很勉强。
10年的东北生活,没什么可后悔的,让我了解了底层的实际情况,心里埋下了很多问题,对意志的锻炼也是正面的。当然,文化上欠亏不少,那属于一个特殊时代,希望以后不会再有了。
高渊:听说你80年代末去美国留学时,英文字母都不认识?
周其仁:我的经历确实有点特别。我在黑龙江时,有7年多是在完达山上当猎人,朝夕相伴的只有一个师傅,到后来见生人讲话都不利索了。大学考到北京后,学的是俄语。后来福特基金会资助我们去美国学习外语,是从abcd开始的。
9个月后,再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有一位研究农村的教授,知道我这些年一直在研究农村,对我特别关照。在那里呆了一年,然后那位教授就给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写了一封推荐信,我没考试就进去念博士了。如果参加考试,至少英语就不可能过关。
高渊:你回国就到了北京大学,10多年后成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创院院长。
周其仁:那是1995年底。当时美国的博士还没完全念完,已经拿到了资格,林毅夫在北大筹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我就回来了。像我这样的个性,本来就不适合到政府机关工作,自由散漫惯了,又不是党员。下海也不可能,我不会做生意,所以去学校最好。
2008年,北大经济研究中心准备升格为国家发展研究院。当时林毅夫恰好要去世界银行当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大家非要我帮老林管这个研究院。我真的做不来行政工作,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当过干部。那几年院里的事情都是其他老师做的,其实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要退休了。根据北大的规定,教授应该63岁退。我打了很多次报告,希望赶快让我退,以后可以承担一些教学任务,重新签个返聘合同,界定权利义务。我相信合约。
高渊:听说你很少接受电视采访,是因为不希望在做社会调查时被人认出来?
周其仁:因为我是一个经验主义者,需要做大量的田野调查,希望越少人认识我越好。如果一个人老在电视上出现,人家不会把他看作一个常人,会产生距离感,不容易说真话。这也是作为当年“杜门学子”所受的熏陶。
高渊:你一直说你是个经验主义者,核心就是一切要从现实出发,要靠自己经验的积累?
周其仁:就是从现象出发,不能从愿望、理想、本本教条出发。我们必须研究现象背后的东西,但前提是先了解现象。有了现象才会有问题,才能探索里面的原因。提出假说,再试验检验它。所以,经验主义并不是与科学对立的力量,它就是科学的方法。
我当年去黑龙江后见到的农民,哪里是报纸上电台里塑造的形象,他们都是为基本生活整天忙碌的普通人。这一课是在农村上的。所以我们先有现象,再有问题,然后来找寻什么理论和办法可以解决问题。当然,没有理想也不行,那就没有一团火。
我现在常跟学生们讲,假定我们从外星球来,我们以为发现了一个问题,地球人却不行动。我们觉得他难受,那他本人不比我们更难受啊?他如果很难受,他为什么没有行动?他不行动,究竟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你顺着这个思路去走,经验主义的路线就出来了。
文章来源:上海观察



